土地是人民生养的根本,也是国家赋税的本源。换句话说,农民是承担赋税的客体。若土地分配真能如同官方文献所载的“一夫百亩”,农民之生计自然不是问题。正是因为均平土地的理想无从落实,架基于其上的赋税,也很自然的成为一个远比土地更加尖锐的问题,且直指农家经营的临界点。

因此,赋税问题只是土地问题下衍生的结果。一般而言,唐代尚属于赋税较轻的时代。但这只是相对而言,稍加观察,便可发现唐代农民的负担仍旧不轻。
唐代最为熟知的赋税便是知名的租庸调法,这是一套与均田制相配合的税制。其赋税的承担者,陆贽已有很清楚的说法:“有田则有租,有家则有调,有身则有庸。”因此,赋税的承担者包括了农民本身与其家庭。

按陆贽的说法,“田租者,言以公田假人,而收其租入,故谓之租。”故可知田租所征收者,乃口分田之属国家所有之公田收益。其负担的内容,依武德二年(619)颁布之命令,则“每一丁租二石。”
可知无论受田多少,每个有受田之丁男皆必须负担二石的田租,故其税率依授得土地之多少有所变动。如能受足口分田八十亩,税率则低达四十分之一;若如开元年间敦煌县效谷乡村民王万寿,其只授得耕地十亩,税率则高达五分之一。若是依最常见的四十亩计算,扣除八亩殖桑的永业田,则税率约在百分之四左右,只有传统理想“什一之税”的一半。

田租执照
调乃所谓“布帛之征”,起自于古代的“贡”,此出农民情感上之自动,如逢年节,向其封君献彘、兔、鸡、鹅或丝布之类。发展的过程中与“赋”相混淆,便从不定期、自动的奉献,渐渐成为定期且强制的征收。故以“调”为名,便带有兴发、调发之意,内涵上与“赋”相同,只是在征收上以“贡”的方式呈现。其负担的内容据开元二十五年(737)的规定,大致如下:

调与租相同,皆为定额之缴纳,无亩数之差异。若二十亩桑田足受,但就绢絁的调率只有二十分之一;若仅得十亩,则高达十分之一。桑树之间的间隔,又可种植些作物补贴开支,王梵志谓:“贫儿二亩地,干枯十树桑。桑下种粟麦,四时供父娘。”可见一亩地中植桑五根,便不至于到“太寡则乏于帛,太多则暴于田。”的窘境。另有棉麻之输,其与绢絁间的折率难以计算,故以开元二十五年令中“其调麻每年支料有余,折一斤输粟一斗,与租同受。”故其支出可列入田租中,将于稍后提及。

布帛
庸是标准的力役之征,也是租庸调法中最为农民所困扰者。其负担的内容如下:

盖劳役多则扰民,故在征收上也有相当的弹性,可以绢代役。若法定的一人二十日全折,需费六丈的绢,比调的征收多出一半。故对一般农民家庭而言,这实在算不上是个轻松的支出。
总体而言,租调两者都还算不上一般农民的沈重负担。田租加上地税户税后的支出,最多也只占粮食作物收入的15%。

绢布
故农民最大的负担来源,是各项力役之征。杨燮便曾这么说过:“今天下黔首不惮征赋,而惮力役。”可见国家征发劳役对于农民骚扰之重。农民对此更是不胜其扰,然而这对于政府而言,却是最难以放弃的一个部分。针对天灾蠲免赋税的规定来看,因灾减免,不是先免役,留下劳力去抗灾抢救,力争较好农业收成,而是规定只有在特大灾害时才免役。由此可见,国家对征调力役是特别重视。
国家对于劳力的征发相当苛刻,实在是“靡室靡家,皆籍其谷;无衣无褐,亦调其庸。”此外,从赴役到服役的路程中间,甚至是服役期间,都必须要自备粮食,规定是这样的:“除程粮外,各唯(准)役赍私粮。”其服役内容,大致上可分作土木营建之役与运输之役。两者皆是造成一片“道路相继,兄去弟还,首尾不绝,远者五六千里,春秋冬夏,略无休时。”

徭役
前者有时甚至有相当程度的危险,如武后在嵩山修三阳宫其间,到了“夫匠疲劳死者十五六。”或许这样的数字本身,便因为张鷟本身的政治立场而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夸大,但也足以表现出劳役繁重的问题了。后者也没好到哪去,甚至有所谓的“脚钱”,大致是这样的:

无由的又多上一条负担。
租庸调法的庸,本身就是力役折换之义,说明朝廷本身便鼓励民众折庸。正因如此,大多数经济状况许可的农民家庭,往往会选择以庸代役。在王梵志〈富饶田舍儿〉里便有生动的描绘:
里正追役来,坐着南厅里。
广设好饮食,多酒劝且醉。
追车即与车,须马即与使。
须钱便与钱,和市亦不避。
然而又有多少农民家庭能经的起这样的负担?针对当时敦煌地区生活状况的考察,在生活线以下的农民占了24%。换句话说,有四分之一的农民生活衣食不足,这样的比例,在今天看来仍旧不低。换句话说,这四分之一的农民很有可能是无力折庸的,他们只能老老实实的赴役,甚至可能选择增加劳动天数,以换取免除租调的待遇。在极端的情况底下,有些人甚至自残躯体,这并非空出臆测,而是可见于实际之记载者,“少慕修道”的空如禅师便是如此,“后成丁,征庸课,遂以麻蜡裹臂,以火爇之,成废疾。”白居易笔下的折臂翁更是生动:

当然,上述的两个例子都只是比较极端情况下的个案,不必太认真看待,多数人还是老实的在许可范围内缴纳赋役。在租庸调法的时代,徭役的征取尚有所限度。两税法之后,虽说将传统的租庸调整合在两税中缴纳,并强调:“此外敛者,以枉法论。”实际上却让人力的征发失去了最底线的依据,力役之征依旧存在。对于贫苦的农民而言,基础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。
在租庸调之外,尚有地税、户税的征收。
首先是地税,其为一种田租以外的附加税。其目的在预备荒年,是统治者为农民设想的一种方式,带有相当程度的储蓄性质,只是以征税的方法表达。其起于太宗时戴冑的建议:“自王公以下,计垦田,秋熟所在为义仓,岁凶以给民。”太宗接纳了这个建议,并发布诏令:
亩税二升,粟、麦、秔、稻,随土地所宜。宽乡敛以所种,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。
“亩税二升”,可见税额相当低,纵使受足额一百亩的口分田与永业田,总共也才不过和田租一样的数额。
户税则是按资产定户等高低,并据以收税的一种方式。从武德六年开始,
天下户量其资产,定为三等。至九年三月,诏:天下户立三等,未尽升降,宜为九等。
其间征复不定,直到武则天长安元年时明令“天下诸州王公以下,宜准例税户。”征复不定,至此方成定制。其税额大概如此:“其八等户所税四百五十二,九等户二百二十二。”
其上的户等之税额则无记载,然很有可能依固定数额一路等加上去,而非以等比级数的方式加成。整体而言,在负担的比例上,依杜佑的说法:
旧制,百姓供公上,计丁定庸调及租,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,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。
只是整体赋税中的一小部分。
以上所说的,都还是较常见的赋税,也是较容易计算到的部分。就以上的赋税计算,扣除日常生活用度,一般农民尚能有“耕三余一”的剩余储蓄。若遇天灾导致收成不良,政府也有一套减免赋税的机制:
凡水旱虫霜为灾,十分损四已上免租,损六已上免调,损七已上课役俱免。
从今日的记载上来看,这并非仅见诸书面的规定,皇帝常常在灾荒之年降敕减免租调赋税,可见这些减免也是经常实施的。
但是租庸调法虽然是广受称赞的良法,却也存在着极大的漏洞。在“量入为出”的财政原则下,租庸调对国家而言是一项纯收入,国家不需要在运输、管理诸环节上有任何花费,计画的租庸调可以完整的到达支用者手上。因为运输与管理的费用,政府已经借由各色名目的加征中获得补偿了。而这当中,更不免贪官污吏的上下其手,使的农民赋税的负担更加难以计算与估量。
参考文献:
- 《陆贽集》
- 《通典》
- 《新唐书》
- 《全唐文》
- 《唐代农民问题研究》
- 《唐代农民家庭经济研究》
- 《国史大纲》
- 《中国古代赋税制度论》
- 《王梵志诗校注》
- 《唐代的力役》
- 《唐大诏令集》
- 《文苑英华》
- 《唐令拾遗》
- 《旧唐书》
- 《龙筋凤髓判》
- 《唐代财政史稿》
- 《新世纪敦煌学论集》
- 《朝野佥载》
- 《太平广记》
- 《白居易集笺校》
- 《唐会要》
本文作者:历史真鉴(今日头条)
原文链接:http://www.toutiao.com/a6692939204969628167/
声明:本次转载非商业用途,每篇文章都注明有明确的作者和来源;仅用于个人学习、研究,如有需要请联系页底邮箱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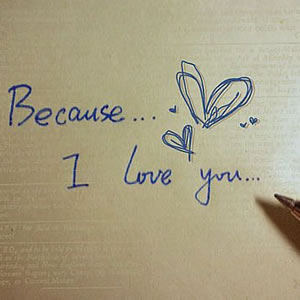
 相同的经济制度为什么能够拖垮西罗
相同的经济制度为什么能够拖垮西罗 元末泸州人刘桢,曾经是农民起义红巾
元末泸州人刘桢,曾经是农民起义红巾 李自成和朱元璋都是农民起义,为何结
李自成和朱元璋都是农民起义,为何结 士风矫激:东汉士大夫政治
士风矫激:东汉士大夫政治 为什么宋朝没有爆发大规模且旷日持
为什么宋朝没有爆发大规模且旷日持 从农民到和尚,朱元璋为何脱颖而出,成
从农民到和尚,朱元璋为何脱颖而出,成 兰州新区出台19条f4的神秘花园措施
兰州新区出台19条f4的神秘花园措施 张伟文在兰州新区东京食尸鬼店长调
张伟文在兰州新区东京食尸鬼店长调 与兰州共美好 融创美好生活首映兰
与兰州共美好 融创美好生活首映兰 以色列—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盒子
以色列—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盒子